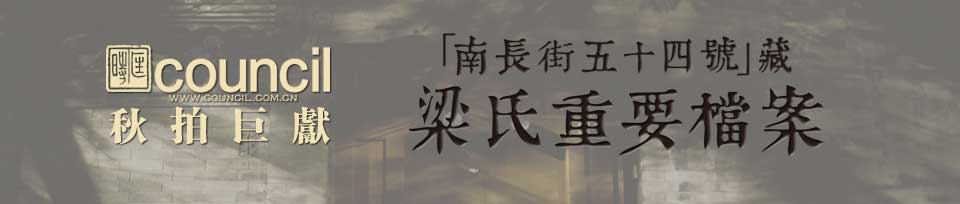——黄遵宪
——毛泽东
——郭沫若
——胡 适
——梁漱溟
——曹聚仁
——刘再复
梁启超、梁启勋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。梁启勋是梁启超的二弟,于诸兄弟中与乃兄年龄相距最近,关系也最亲密。1890年,梁启超结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。1891年,在梁启超、陈千秋的邀请下,康有为在广州设立“万木草堂”,梁启勋于1893年随兄入“万木草堂”学习,学得许多西方哲学、历史和自然科学技术,还自学英、日文。
1896年康有为、梁启超在上海办起《时务报》,公开提出变法的主张,梁启勋任该报的编辑,主要负责翻译和编审东西文译稿。1898年光绪帝宣布变法,遭到以西太后及保守派的抵制干扰,后维新派被袁世凯出卖,西太后囚禁光绪帝,并通缉变法分子,康有为、梁启超逃脱,许多同仁被杀害。在危急时刻,梁启勋把在二线尚未被通缉的同志组织起来,紧急抢救掩护被难同志的家属,扶老携幼逃向澳门、香港和国外。为了摆脱捕快们不断地跟踪追缉,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次,身担如此巨大压力和紧张的抢救工作,使他患上了神经性头痛达10年之久,数十年后,麦孟华、罗孝高等一些老友见面时还戏称他为“家属队长”。
1912年梁启超与梁启勋一同回国,返回天津,梁启超着手创办《庸言报》,梁启勋任报纸撰述。1914年,梁启超任接任币制局总裁,梁启勋即任中国银行监理、币制局参事的经济工作等。1915年梁启超主编《大中华》杂志,梁启勋任杂志撰述。1916年,护国战争爆发,梁启超南下发起反袁活动,梁启勋在广州料理父亲梁宝瑛丧事,梁启超开始不知父亲逝世消息,仍寄来报平安的家信。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, 4月29日,英、美、法三国作出决定,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权利让与日本。梁启超致电林长民,林氏刊文说明事实,导致五四运动爆发,这其中,梁启勋赠千金给被捕的学生。1924年,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,梁启勋在北京全权负责营造墓园工程。1925年,梁启超在清华讲学期间,进城便住在南长街梁启勋住所。1926年,梁启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,聘梁启勋为总务长。1927年,梁启勋代梁启超在北京为梁思成、林徽因主持订婚仪式。1928年,梁启超因病住在协和医院,梁启勋写有《曼殊室戊辰笔记》。1929年梁启勋于梁启超逝后跋《袁世凯之解剖》、《白香山诗集》、《东坡乐府》、《初白庵苏诗补注》,缅怀长兄。
梁启超著作结集为《饮冰室合集》,梁启勋没有全集,著作有《海波词》四卷、《词学》二卷、《辛稼轩词疏证》六卷、《曼殊室随笔》等。梁启超早年流亡日本时,梁启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,兄弟之间常常鸿雁往来,探讨学问之道。及至1912年梁启超回国,梁启勋则成为乃兄负责家庭事务的左右手。梁启超对诗词的研究兴趣,对梁启勋影响很大。今人陈声聪以梁启超昆仲比拟苏轼兄弟,殊为确当。梁启勋的《稼轩词疏证》正是继长兄梁启超未竟之业,并对乃兄的研究成果进行补正。
1891年广州市长兴里新开办了一家学堂,取名万木草堂,先生就是日后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维新派主脑康有为,万木草堂宣传维新、改良思想,从创办初期的学生不满20人,到后来的100多人,这里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维新变法的人才,其中梁启超、麦孟华、陈千秋、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。汤觉顿和梁启勋即在梁启超的介绍下入“万木草堂”学习。是时梁、麦同寓,时常“相与规划救国政略,并助南海先生奔走国事”。
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一时间在京赴考的学子群情激奋,康有为等联合各省举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运动,此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,组织维新力量,讨论“中国自强之学”。近代史上励精图治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展起来。1896年梁启超、黄遵宪、麦孟华在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,梁启超任主笔,以变法图存为宗旨,连载梁启超著《变法通议》。
戊戌变法失败后,康门师生流亡海外仍坚持开民智、兴民权的政治改良运动。1989年梁启超与麦孟华一起创办《清议报》,撰写宣扬保皇的文章,提倡学习日本维新,增强国力以救亡。汤觉顿此时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,陪同康有为、梁铁君等人前往新加坡侨处理保皇会事务。1901年《清议报》被迫停刊后,梁启超在横浜创刊《新民丛报》,“取《大学》‘新民’之意,以为欲维新中国,当先维新我民”, 连载了对青年一代影响深远的《新民说》,介绍民主、自由等思想。并且与革命党的机关报《民報》展開長期論戰。梁启超撰稿不遗余力舌战群雄,虽然双方笔战不断,但从客观上共同传播了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思想,从此梁启超声名鹊起,奠定了他“言论界骄子”的地位。麦孟华则担任编辑和撰述的工作,在推进“新文体”的编辑、传播中他功不可没。虽然梁启超声誉日隆,但梁、麦两人的友谊并未发生变化,因为同时蛰居日本、创刊办报,可谓患难之交,在麦孟华不多的诗词中有多首与梁启超的应和之作。
在国内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,梁启超于1907年在日本成立立宪团体“政闻社”,创立《政论》为机关报,继续推进君主立宪运动。1908年2月,政闻社迁往上海,汤觉顿、麦孟华亦回到国内开展工作,积极动员当朝权贵,汤觉顿是奔走其间的重要人物之一。作为政闻社的灵魂,梁启超对政闻社的控制,实多通过汤觉顿这一纽带来完成。
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,梁启超、康有为先回到国内,此时他们的政治意见出现分歧。康有为身居上海反对共和制,继续宣扬尊孔复辟。而梁启超则积极拥护共和政体,1913年与梁启勋一起定居在北京南长街54号,并参与新政府的政治活动。同年推荐汤觉顿出任中国银行总裁,认为“此机关为全国财政命脉所系,非以极远之眼光,极敏之手腕,不能絜其枢以振衰敝”,并力促觉顿任之,梁启勋也在其中任职。麦孟华则一直在上海,与梁启超相隔千里。由于内心的忧虑及身体的孱弱拒绝出任教育总长等职务,梁启超则常写信宽慰他低沉、忧郁的心情。
1915年2月麦孟华因病突然辞世,梁启超闻后“五内崩裂”,当日即作《哭麦孺博诗》,前后八首,又作祭文,并代抚其遗孤,可见二人友谊之深厚。同年秋月,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日益暴露,梁启超、蔡锷、汤觉顿开始秘密筹划倒袁运动。梁、汤与蔡分两路南下,蔡锷回到云南宣布独立,而梁、汤则积极奔走联合其他各省势力筹划滇、黔、桂诸省的举义。同时,汤觉顿赴南京联络冯国璋,广州的孙中山、岑春煊等各派势力,建立起广泛的反袁 “统一战线”。1916年春,广西独立、袁世凯也被迫取消帝制,护国战争朝好的方向慢慢转化,粤军首领龙济光邀陆荣廷和梁启超赴海珠商议和平解决广东问题,汤觉顿深知“粤不定则贼不灭”,故以特使身份亲身赴粤,却中圈套而被杀害。得知消息后梁启超悲愤满怀,挥笔写下了《祭海珠三烈文》。多少年来,为了这位蜚声国内外、赤心为国的师兄,汤觉顿几乎舍却“私己”,把梁启超当作自己事业的中心,代之历险阻,为之洒血汗。他在挽觉顿之联中写道:
纳公规若毫髮,贻公谤若丘山,不祥如余,愿世世勿相友;
尽其力为张良,洁其身为龚胜,非命而夺,疑苍苍者匪天。
在广州公祭梁启超再次缅怀觉顿之风仪,哭曰:“公固为国死,亦为启超死也!”梁启超广交朋友,师友遍天下,但像汤觉顿这样长期相伴、无间亲密者也只有汤氏一人;对汤氏来说,平生知交,则无出梁氏之右者。